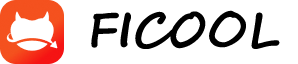清晨五点,天刚蒙蒙亮.河内的酷热经过一夜雨水的冲刷,暂时被一层稀薄的凉意取代.同塔梅区的出租屋区尚未完全苏醒,只有早起打工的人们发出的零星声响.巷弄里到处是昨夜暴雨留下的水洼,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味.阮文轻手轻脚地起身,生怕吵醒另一张床上刚刚咳喘平复,好不容易入睡的母亲.妹妹阿梅蜷缩在角落里的小床上,书本还摊在枕边.
他简单洗漱,冰冷的自来水浇在脸上,让人彻底清醒.看着镜子里自己年轻却已刻上生活风霜痕迹的脸,他深吸一口气.厨房里没有生火的迹象,母亲的身体已经经不起烟熏火燎了.阮文拿起昨晚买的两个冷硬的"bánh mỳ"塞进书包里当午饭,又从抽屉深处一个破旧的小铁盒里,数出几张数额不大的纸币——这是他身上所有的现金,是给陈先生返程的车资预备金(以防平台抽风或客户不用App支付).他对着角落里一张模糊的父亲遗照轻轻拜了拜,带上头盔和车钥匙,再次推着他那辆被擦干净但挡泥板边缘仍残留着干涸泥痕的老伙计,驶入了黎明前微凉的街道.
从同塔梅区赶往嘉林县同进村的路途在微曦中显得清晰却也漫长.早班公交已经开始运行,拖着长长的乘客队伍;人力三轮车夫已经蹲在街角,等着第一单生意;穿着制服的工人骑着车沉默地奔向各个工业区.空气中是特有的混合气味——路边摊贩刚刚升起的炭火烟味,河内清晨独有的米粉汤(Phở)的香味,还有垃圾尚未清运完毕的发酵气味.阮文穿梭其间,心情意外地比往日平静,昨夜那张十万盾带来的微光,和那个神秘陈先生的约定,像一个谜,暂时掩盖了债务的阴云.
六点五十分,他准时停在了陈先生院门口.那棵高大的芭蕉树叶子在晨雾中舒展着,翠绿欲滴.土地庙前残留着昨晚的香灰.陈先生已经等在那里,依旧穿着简单,一件干净的米白色衬衫,深色裤子,背着个看起来用了很久的帆布包.
"陈先生,早上好."阮文打招呼.
"早,小阮."陈先生点点头,脸上没什么倦容,他拉开院门,推出来自己的摩托车——就是昨晚阮文帮忙修好的那辆,擦得锃亮."我骑车跟着你吧?这样你不用走回头路送我,省油省时间."
阮文有些意外,随即点头:"也好.我给您带路."他没问陈先生为什么不开车或者打车,这个男人的逻辑似乎和常人不同.
两辆摩托车一前一后,沿着昨夜的泥泞路,朝着巴亭广场的方向驶去.清晨的嘉林郊外水汽氤氲,稻田绿意盎然,偶尔有白鹭掠过水面.当车子驶上横跨红河的龙编大桥(Cầu Long Biên)时,视野豁然开朗.大桥是钢铁巨构,充满了法式殖民时期的沧桑痕迹,桥下是宽阔,浑黄,裹挟着上游泥沙奔涌的红河河水.清晨的薄雾像一层轻纱覆盖在河面和两岸参差的建筑群上,河内老城区的一片片黄色法式建筑屋顶在雾气中若隐若现,古老与新潮在这里奇异地交织.
"这桥很老了,比爷爷的年纪还大."阮文主动开口介绍,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这座城市底层历史的熟悉感,"以前战乱时被炸断过好几次,都修好了."
陈先生骑着车跟在后面,闻言稍微靠近了些,望向桥下的红河和对岸的城市轮廓:"嗯,一座有故事和韧性的桥.河内的脉络,由这水,这桥,还有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构成."他的目光悠远,像是在看桥,又像是在透过河雾看别的东西.
接近还剑湖边的还山市场(Chợ Hàng Da)时,时间还早.市场已经开始喧嚣起来,各种摊位前人头攒动,空气中弥漫着热带水果浓郁的甜香,新鲜海产的腥气,香料堆的强烈刺激以及现煮咖啡的醇厚焦苦味.小贩们的吆喝声,讨价还价声,摩托车的喇叭声混合成交响乐.食物的香气也浓郁起来:冒着热气的法棍三明治,香气扑鼻的越南煎饼(bánh xèo),摆得满满当当的鲜虾春卷(gỏi cuốn)...
"陈先生,您吃早饭了吗?我知道一个摊位,'蟹肉汤粉'(Bún riêu)做得不错,就在市场里面."阮文停好车,主动提议.他肚子有点饿,书包里的冷法棍实在不想碰,而且他觉得带这位"穷游客"尝点真正的本地美味,算是自己力所能及的感谢.
陈先生笑了,这是阮文第一次看到他脸上露出比较明显的笑意:"好,尝尝本地人吃的,好过酒店里的."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或挑剔.
两人找了个街角摊位最角落的位置坐下.塑料凳子很矮小,折叠餐桌油腻发亮.阮文点了两碗最经典的蟹肉汤粉,加了油条(quẩy).很快,两碗热气腾腾,色彩丰富的米粉端了上来:橙红色的蟹肉番茄汤底,鲜嫩的蟹肉丸,炸得金黄酥脆的豆腐泡,几片新鲜猪血,翠绿的葱花飘在汤面上,香气霸道地钻进鼻腔.
陈先生没有客套,拿起筷子就吃,动作不急不缓.他尝了一口,眼神亮了亮:"嗯,汤头鲜浓,蟹肉新鲜,味道很好."他吃得专注,不时点头.旁边坐的都是本地劳工,小贩,或穿着廉价工装的上班族,没人多看他们一眼.
阮文也埋头吃起来,冰冷的身体被这碗热腾腾的粉汤迅速温暖.他吃着吃着,目光习惯性地扫过街对面.那里停着一辆崭新的,价值不菲的本田SH摩托车,擦得锃亮,车主是一个穿着时髦衬衫,头发梳得油亮的年轻男人,正坐在一个看起来干净高档很多的咖啡馆露天座上,和一个同样打扮靓丽的女孩谈笑风生.那人似乎注意到了阮文这边环境嘈杂,食客普通,眼神掠过时,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和疏离,眉头微微皱了一下,仿佛这边的气味和人群污了他的空气,接着就转过头去,继续和女伴谈笑.
阮文感觉到了那目光,喉咙里的粉汤似乎哽了一下.他若无其事地低下头,继续吃.这目光他太熟悉了,和昨晚开Fortuner的金链男,以及订外卖的北方大妈一样,仿佛他和他所处的这个世界,天然低人一等.他把注意力放回眼前的汤碗里,这碗十几万盾就能温暖身心的粉汤,是属于他和陈先生,以及眼前这些为生计奔忙的普通人的.
"那个人,"陈先生放下筷子,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街对面那个骑SH的青年,声音不大,刚好阮文能听见,"你觉得,他那辆车能买多少碗这样的好粉?"
阮文愣了一下,没想到陈先生会问这个.他默默心算了一下:"大概…五六百碗?或者更多?"那是一笔他暂时不敢想象的巨款.
陈先生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嘴(纸巾质地粗糙),目光平静地看向阮文:"小阮,你有想过吗?一碗粉卖三万五千盾,他赚走了利润的一部分.但制造一辆那样的摩托车,组装它的工厂赚走了利润,卖车的店赚走了利润,设计研发的企业赚走了更多的利润.最终,这些利润的大部分,会流回到哪里?"
"工厂的老板?经销商?还有…国外的总公司?"阮文努力思考,他能懂机器运转,但对钱流动的轨迹却很陌生.
"对,也不全对."陈先生点点头,"它们流向了资本的源头,流向了那些提供原材料,技术专利,核心设计和整合渠道的人.他们不见得是骑在车里享受的人,他们是推动这辆车运转的人,坐在写字楼里,或者投资银行办公室的人.底层劳动者,比如这做粉的阿婆,"他示意了一下正忙碌的摊主,"还有你和我这样的服务者,运输者,拿到的是辛苦钱,是链条最末端的一部分.我们参与其中,但很难分享链条前端创造的巨大价值."
阮文似懂非懂,这些话超出了他的认知.他有些茫然地看着陈先生.
陈先生没有深入解释,转而问道:"你每天跑车,很辛苦,收入都覆盖支出吗?或者说,除掉所有生活开销,你一个月能攒下多少结余?"
这个问题直戳阮文的痛处.他嘴角泛起一丝苦涩,声音低了下去:"哪有什么结余…陈先生.家里妈妈病着,吃药是钱;妹妹读书是钱;租房子要钱;油费,修车,平台抽成…现在外面还欠了一大笔债.别说结余,能不欠更多,就很好了."他下意识摸了摸胸口,仿佛还能感受到那张湿漉漉的十万盾的存在.
陈先生沉默地点点头,眼神中没有任何评判."债务是多少?"
阮文迟疑了一下,但这几天的接触让陈先生显得莫名值得信赖:"三…三千万盾.已经拖了一阵子了."说出这个数字让他觉得沉重.
"三千万…"陈先生轻轻重复了一遍,"那你想过,除了卖力气和时间,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让钱生钱?哪怕一点点小的钱?像一颗种子?"
阮文困惑地摇头.钱能生钱?那是银行家的事,是高利贷的事.他只知道钱是辛辛苦苦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.
"比如,"陈先生看向远处高楼林立的区域,"你觉得河内像不像一块被用力锤打的钢铁?"城市在晨光中显出轮廓,"锤打中,有些地方会变得更硬实(发展区),有些地方会留下缝隙,凹陷(被遗忘的老城区).敏锐的人,能看到这些缝隙和凹陷里暂时被忽略的价值.如果现在在那些看起来混乱,落后,但交通已经开始改善,或者有大公司计划搬迁过去的地方,买下一套老旧但位置不错的小房子,或者一小块别人觉得没用的地皮,花不多的钱修缮一下,等城市的大锤敲打到那里,缝隙被填平,凹陷被撑起时,它原来的位置和价值,是不是就不一样了?"
他用筷子沾了点水,在油腻的桌子上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."这就是投资,投资未来城市变化的趋势.它需要眼力,需要判断,更需要耐心,还有启动的'种子'.种子可以很小,五千,一万,甚至十万盾,但方向要对,要在改变发生之前埋下去."他看了看阮文,"这比日复一日只靠消耗体力换取现金,更能让钱为你工作,而不是你一直为钱奔命."
阮文的心,被重重地敲击了一下.这番话,如同一道微弱却清晰的电流,在他困顿的世界里划过一道光,照亮了他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.他怔怔地看着桌子上陈先生用水画出的那个简陋的地图——买下被遗忘的缝隙…等待城市之锤把它变亮…
"我…我这样的人…哪有钱去做投资?连种子钱都没有."阮文的声音干涩.
陈先生擦掉桌上的水迹,眼神深邃地看着他:"种子,有时不一定非得是现金.它可以是你对这座城市的了解,是你比别人更懂得哪些地方在变,怎么变的嗅觉,是你从底层锻炼出来的韧性,耐心和解决问题的勇气.钱是表象,能看到价值洼地的眼光和敢于行动的心,才是真正的种子."
早餐摊的嘈杂声似乎在这一刻远去.巴亭广场方向传来了悠扬的升旗乐声,新的一天正式开始了.阮文看着眼前这位平静吃粉的"中国穷游客",只觉得胸口鼓胀,仿佛有什么东西,正在他贫瘠已久的心田深处,怯生生却又顽强地,破土而出.
他第一次觉得,这城市的雾霭里,似乎藏着一缕微光,指引着一条他从未看清过的路.而这条路的起点,可能就在这张油腻的小塑料餐桌上.